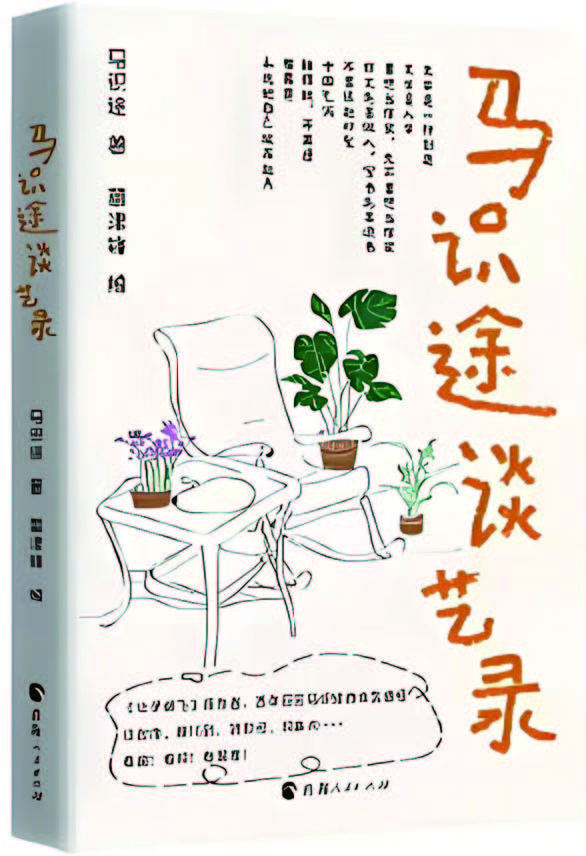文学,生命的滋养与升华
—— 读《马识途谈艺录》有感
□ 刘清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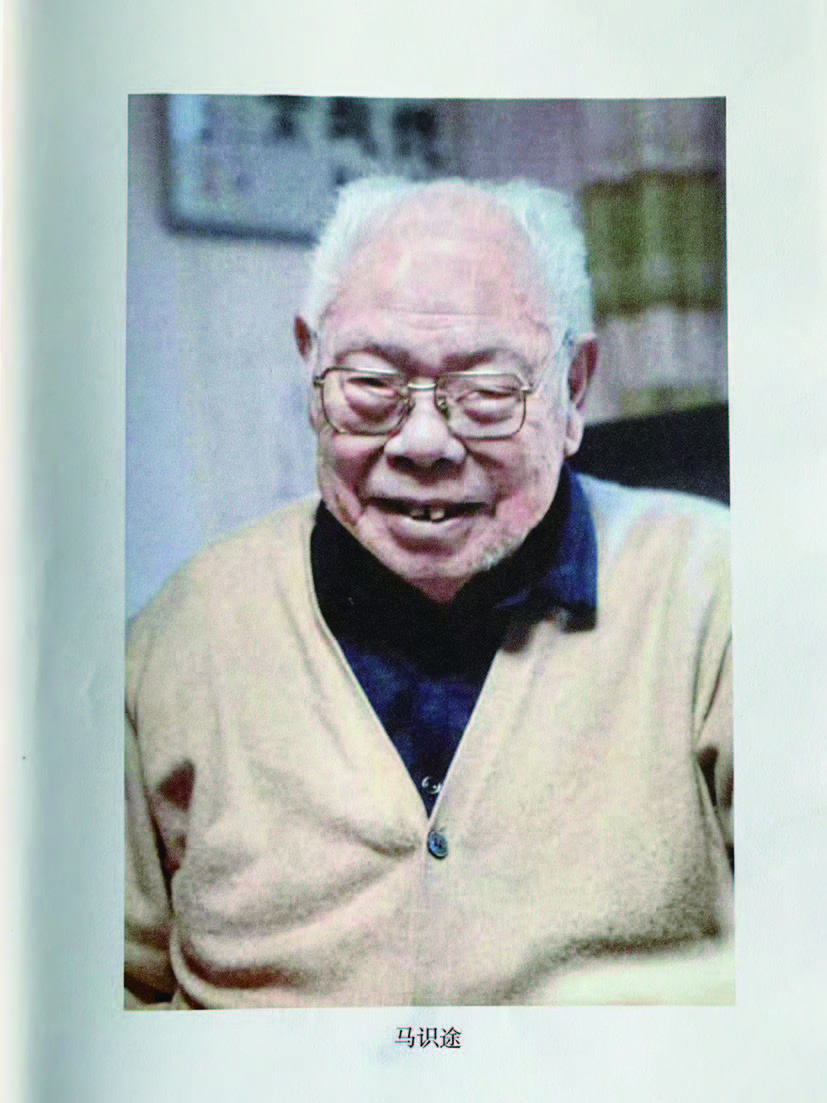
与文学的相遇,于我而言是一场意外而必然的邂逅。偶然刷到的《马识途谈艺录》获奖消息,却让那些充满生命力的文字叩击心灵——这恰印证了文学滋养生命的奇妙:看似偶然的触动,实则源于人类对精神家园的永恒追寻。当生活琐碎如茧,文学恰是破茧的刀刃,让我们在文字构筑的避风港中,窥见生命更辽阔的维度。
马识途先生的人生恰是文学与生命交融的典范。他在《谈艺录》中提出的“生命延长”理念,与巴尔扎克“时代书记”的文学观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:前者强调以文学突破生命物理局限,后者侧重用文字镌刻时代精神。这种双重维度恰是知识分子的使命——既需在有限中创造永恒,又要让文字成为映照时代的明镜。马识途九十二岁罹患肺癌仍笔耕不辍,病房中的创作既是与死神赛跑的生命抗争,更是将革命精神注入文学的壮举。司马迁著《史记》的坚毅,在他身上化作抗癌书写的当代寓言,让《夜谭续记》中民间人物的豁达智慧,浸染着创作者自身的生命韧性。
细究其创作历程,可见三重生命境界的跃升。早年战火纷飞中,文学是他突破现实桎梏的羽翼:在《夜谭十记》的创作中,动荡岁月里的辗转反侧皆化作纸间风云,文字不仅是表达载体,更是让精神在想象中永生的方舟。中年沉淀期,他将革命者的热血与学者的理性熔铸成独特的讽刺美学,西南联大的学术训练让笔锋既具现实穿透力,又不失智性光芒。晚年病榻前,甲骨文研究成为文化传承的自觉担当,壹佰零柒岁完成的学术笔记,将个体生命与文明血脉紧密相连。从“呐喊”到“沉思”的轨迹,既是个人命运的起伏,更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启蒙到寻根的嬗变。
《谈艺录》揭示的文学观,实为四重精神维度的交响。其一,视文学为革命精神的永恒载体,将“经国大业”的宏愿融入字句;其二,以写作复活烈士精魂,让历史记忆在文字中永生;其三,坚信文学净化灵魂的力量,《夜谭续记》对人性的洞察如手术刀般精准;其四,晚年学术创作延续文化薪火,践行“生命不止,求索不息”的誓言。这种将个体生命与民族精神相系的情怀,使他的创作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。
在雅俗之辩中,马识途的探索尤为珍贵。《夜谭十记》构建的“书场叙事”,让革命者的现实洞察与传统说书艺术碰撞出火花。这种雅俗共赏的智慧,为当代文学指明方向:当网络文学以新媒介延续俗文学血脉,我们更需思考如何让“爽感”不止于麻醉,而是如盐入味般将文化精髓融入叙事。马识途以“俗文学观”调和雅俗的对立,既延续“五四”启蒙精神,又激活民间文化基因,这种辩证思维对当下文学创作仍具启示。
“人性如夜谭,黑处愈黑,光处愈光。”马识途的箴言道破文学的本质力量。当现实的牢笼禁锢肉体,文字便成为打开精神自由的密钥。从抗日烽火中的丧妻之痛,到抗癌病房里的生死时速,他将生命体验淬炼成文学养料,让《夜谭续记》既是革命史诗,更是生命哲学的结晶。这种“用生命书写生命”的创作观,成就了文学风格与生命态度的完美统一。
站在如东县老年大学“春之声”读书节的节点回望,文学对生命的滋养恰似春泥护花。它既在偶然的相遇中播撒种子,更在必然的成长中培育精神年轮。当我们在文字中触摸马识途们的精神轨迹,便是在有限生命中开辟无限可能——这或许就是文学最深邃的魔力:让每个平凡生命都能在阅读与书写中,完成属于自己的精神涅槃。